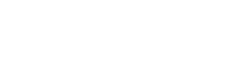文: 李淼(英语语言文学副教授、翻译家、英国约克大学文学硕士)
我是看过泗伟画的第一匹马的。几年前,那时的泗伟还在寻找自己绘画语言的否定再否定的探索期,在泗伟工作室,我看到一幅关于马的新作。那匹马的眼神,理性、疏离、冰冷,但你却能感受到它内在涌动着热切的、势不可挡的情绪。我当时就惊呼:“这匹马简直就是泗伟的自画像!”昨天,当泗伟把他的《守望者》、 《逐梦者》系列一张张发给我的时候,我有点激动,一方面是为多年好友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为我自己先知般的慧眼。
泗伟画的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不是抽象或写意,但也绝非自然写实。他有时缩短了马的头颈比,有时又拉长了头颈比,还有一些马被褪去了鬃毛。泗伟的马都是对头部的刻画,而他的每张画上的灵魂之笔,都是在马的眼睛的刻画上。
他的《守望者》系列中的马,好像是刚刚出土的古代雕塑,笔触粗犷,线条坚硬,马的身上都是岁月侵蚀的裂纹和斑驳痕迹,覆盖着一层穿越时空的灰尘。那些眼睛,或暗淡、或惊恐、或绝望,仿佛刚刚从死亡的战场归来,看尽了沙场屠戮,刀戟厮杀。他们是历史的守望者,也是历史的牺牲品。他的《逐梦者》系列中的马更像现实中的马,画面简洁,笔触细腻。但是马的眼睛却仿佛看透了现世,呈现出忧郁、理性,又冰冷、疏离的眼神!这就是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里境遇吧。
马,一直以来都是画家、诗人、文学家,甚至电影的重要题材。不管是作为生活中的劳动力,还是战场上的助力,马在中西方都享有相当高的地位。人类对马的推崇总是盛行于历史上开疆拓土的时代。据说汉武帝对马的喜爱程度,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得到宝马,他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并亲自为自己的汗血宝马作《天马歌》进行颂扬。与汉武帝几乎同一时期的亚历山大帝,也有在12岁时驯服一匹名叫布塞菲勒斯的名种马的传奇故事,据说此举令其父断言此子绝不仅仅属于马其顿,他一定可以成就更大的伟业。唐太宗生前出征各地所骑的马匹,在其死后,都有雕像保存下来,放置在唐太宗的墓中,总共有六匹,称为《昭陵六俊》。拿破仑一生拥有超过150匹马,他留下来的大部分画像都是和自己的战马在一起。由此可见,在历史上,马,代表着国家的国威和兵力,也代表着人的威严和权力,有着特殊的隐喻意义。
而到现当代,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以马来隐喻时代,映照人性。比如:徐悲鸿的《奔马图》。抗战爆发后,徐悲鸿意识到国难当头,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中,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所以他的马昂首奋蹄,鬃毛飞扬,强健有力,象征着正在觉醒的中华民族精神。还比如一部2014年的电影《狂怒》,在影片的开场,一个固定长镜头从昏暗到旭日东升,画面中心,逆光而来一名骑着白马的军人。当画面渐渐清晰,原来是一名纳粹军官,骑着白色战马,淡然的走在遍布盟军尸体的战场上。此处纳粹军官与白马,象征了纳粹泰然自得的践踏人命,进行泯灭人性的暴行。与此同时,埋伏在几步之遥的盟军队长 Wardaddy果断突袭,几刀毙命,将其拉下了马。寓意深刻的是他从白马身上卸下缰绳,并目送这匹白色的战马,从荒芜的战场中远走。这样的开头正契合了人物的信念与影片主题,“打击纳粹,解放人类,让人性回归。” 很多影评人说:“片中的开场白马,象征了人性! ”
所以,马,到了泗伟这,又被赋予了更多的与时代相关的、与精神相关的寓意。泗伟的马只有头颈部分,没有躯干,我觉得画家是故意的,他在有意识的 将观众导向对马本身的关注,对马作为一个独立生物存在的关注,或者是对马的思想与情感的关注。至于马背上的人,他觉得不重要,也许他很鄙视。透过马的眼睛,我们能看到它们对过往的惊恐和绝望,对梦想的迷茫和忧虑。那么,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有没有看到被囚禁在冰冷的石头里的你的灵魂?有没有看到被剃去了鬃毛失去了风雨庇护的能力的那个被阉割了的你?如果你没看到,那就盯紧这些马的眼睛,那是人性与灵魂触及的唯一窗口。
海子有一首诗,与泗伟此次的展览同名----《以梦为马》。也许泗伟碰巧读过,碰巧生出了共鸣,我没有确认,也不需要确认,伟大的灵魂不需要相遇,他们在各自的时空闪亮,而这些光芒总会在某些时刻,穿越历史的尘埃,在某处交汇。
海子说: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踢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
泗伟手中的画笔,即是永恒的事业!
点赞 0 浏览 197
-
 《遇见你的忧伤》 布面油画/2023
《遇见你的忧伤》 布面油画/202340 x 60 cm | ¥ 5,600
2.1 -
 《坠落的风筝》 布面油画/2023
《坠落的风筝》 布面油画/2023100 x 60 cm | ¥ 24,000
2.0 -
 《痕-1》 布面油画/2023
《痕-1》 布面油画/202330 x 30 cm | ¥ 3,600
2.0 -
 《痕-2》 布面油画/2023
《痕-2》 布面油画/202330 x 30 cm | ¥ 3,600
2.0 -
 《痕-3》 布面油画/2023
《痕-3》 布面油画/202330 x 30 cm | ¥ 3,600
2.0 -
 《痕-4》 布面油画/2023
《痕-4》 布面油画/202330 x 30 cm | ¥ 3,600
2.0 -
 《痕-5》 布面油画/2023
《痕-5》 布面油画/202330 x 30 cm | ¥ 3,600
2.0 -
 《关于彼岸》 布面油画/2021
《关于彼岸》 布面油画/2021120 x 60 cm | ¥ 24,000
2.0 -
 《聆听你的孤独》 布面油画/2019
《聆听你的孤独》 布面油画/201950 x 40 cm | ¥ 5,600
2.0 -
 《痕-6》 布面油画/2023
《痕-6》 布面油画/202330 x 40 cm | ¥ 3,600
1.9 -
 《惊鸟》 布面油画/2024
《惊鸟》 布面油画/202440 x 60 cm | ¥ 5,600
1.9 -
 《谁在孤独时与你为伴》 布面油画/2024
《谁在孤独时与你为伴》 布面油画/202440 x 60 cm | ¥ 5,600
1.8 -
 《今夕何年(之二)》 布面油画/2021
《今夕何年(之二)》 布面油画/2021120 x 60 cm | ¥ 24,000
1.8 -
 《今夕何年》 布面油画/2021
《今夕何年》 布面油画/2021120 x 60 cm | ¥ 24,000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