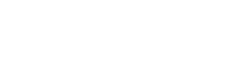文_诸葛沂
美国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在名篇《抽象艺术的性质》中曾写道:“写实的作品不是靠了与自然的相似程度来确保其美学价值,抽象艺术也不是靠了它的抽象或‘纯粹’来确保其美学意义。自然形式和抽象形式都是艺术创作的材料。”确实,以绝对的“纯粹”和极端抽象性来囊括所有类型的抽象艺术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真正的抽象艺术家都不是在创造一种绝对的形式,而是在穿越情绪之海的航程中持续描绘精神风景。
胡昤,就是当下中国青年艺术家之中,将抽象绘画执著地建立在个人阐述基础上的独特画家,其绘画传达出的既不是那种刻意拒斥图像的边缘体验,也不是对于不确定性过程及类似“参禅”活动的个人体验,而是一种真实而自由的生命解释。
当画布成为像胡昤这样的艺术家面对的物体时,它便渐渐脱离了物性,成为展开在胸前的海洋,只有自由如精灵般的舞者,才能解开心灵的枷锁,恣意畅游这深且广的无垠天地。在胡昤的画作中,你看不到一丝僵化的印迹,到处是灵动,是闪现,是念呓,有时,甚至还有一丝独步悬丝的玄想,一点独舞宙宇的冥思。
胡昤的这种自由,仿佛不是经由“解放”而来的后果,反倒是天生的,没有烙痕的,没有目的性的,没有企图的,尽管在画作中存在某种情绪上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也是自主的,自发的,自为的。在她的天地里,她是唯一的观看者,唯一的探索者,这种唯一性产生了更纯粹、更达观的精神性,而这与“是不是抽象的”毫无关系。因为抽象不再是目的,而是自如开翕的生命,就如蜗牛的触角一般敏感,如夜色褪去一般自然。
我之所以将“镜”赋予胡昤绘画为第一层含义,绝不是强调再现在其作品中的地位,而是突出其画作中折现出的那些林林总总的独立的“象”,是如何在呈现于观者的过程中触动心扉,并将他们引入梦一般的境界之中的。
康定斯基抽象画强调心境,认为最终的图像是从内部投射出来的,是其心境完整性及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具体证据。而我认为这种投射的形式万千,并处于流动的变化之中。无疑,胡昤早期的画作中存在着让我们似曾相识的形象,或是一个迷离的梦的细节,或是一个斑驳的生活碎片,它们静默地展现,缄默不语,它们在不同的维度盈亏与消长,在模糊了物像时潜意传念,这种迁流的微缩景观幻化了世界的现实经验,勒止了观者固执的追问,使最活跃的观众最终和艺术家一道在画作中通过“幻”见到“真”,并复归平静。这就是“镜”在某时刻的效果——好比一个狷夫怒骂时突然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嘴脸——这种震动源自于突遇真相的回思,直觉情绪扑面而来。
最近,胡昤的画作明显表现出了某种转变。当时间浸透渗漶进生活之后,胡昤已经走到了艺术的另一边。她捡起个人生活中已被使用或废弃的材料,听:它们发声了。物本体接托了思想的虚体,却在凝视中生成了观念的实体。正如哈曼所说,主体与物自体的对话,导向了这个世界当中的本体。胡昤走到了另一层境界:触摸时间。
在胡昤的另一组作品当中,对时间的触摸,以一种谦虚的姿态,邀请观者进入。在创思和制作的过程当中,时间从思绪、笔触、材料的呼吸当中现出本真性。存在不再仅仅是艺术家主动的开启,而是一种连贯的、接续的和生成性的书写。这并不是时间的偶然,而是时间的必然。她抓取到了这种必然。
“礁”是坚硬的,连绵的,冷静的,又是执著的,坚定的,在被冲击的浪涛中岿然静伫,但却能够迸发巨大的能量。胡昤虽然是一个柔弱的女画家,但其画作却透露出元素之间的对立,情绪之间的分裂,或在望眼欲穿的梦幻图像中闪现突兀的现实,或在画面上以冷暖静动的对比推动某种情绪的对比。从这个角度上看,胡昤确实是在清醒而孑孑的作画,并没有坠入“空无”的识见之中,而是对自然、生活甚至社会的真实情感、深刻体悟,这就让画面往往呈现开合大度又直指心扉的力道。
当现实生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平面化,当现实中众多带有功利性的图像瞬息万变地掠过人的眼球,占据头脑与心灵,人变成非人,并被推到了丧失内心自由的境地,表象的记忆稍纵即忘,本质的情绪无从捕捉。这时,胡昤的绘画给出了艺术救赎的实质意义,它把表象模糊化的失忆抽象再现,将那种被逼自边缘的现代人的自由恣意表现,真正的会意者将在观看中领会那份“真”与“幻”的体悟,“镜”与“礁”的对语,带点失意、跃动、沉湎,甚至讽刺,在沉浮之间静观万相,最终获得一种对自身主体自由的叩问。这也许可以是艺术最终的目的。
艺术是谎言,但却述说真理。
胡昤,这个自由飘逸的精灵,还在她自己广袤而深邃的森林里游走,在巨大无垠的海域里潜行,她的画笔在自由地发展,就像枝条伸展,再伸展。她说:没有彼岸,便有自由,执念彼岸,便失自由。
我想,她算是看清了艺术之于生活的价值。
点赞 0 浏览 178
-
 《时光书写No.6》 布面综合材料/2020
《时光书写No.6》 布面综合材料/2020160 x 160 cm | ¥ 110,000
2.2 -
 《时光书写No.8》 布面综合材料/2020
《时光书写No.8》 布面综合材料/202030 x 30 cm | ¥ 20,000
2.0 -
 《无题》 布面综合材料/2020
《无题》 布面综合材料/202030 x 30 cm | ¥ 20,000
2.0 -
 《时光书写N0.19》 布面综合材料/2021
《时光书写N0.19》 布面综合材料/202130 x 30 cm | ¥ 20,000
2.0 -
 《时光书写1》 布面综合材料/2019
《时光书写1》 布面综合材料/201930 x 30 cm | ¥ 20,000
2.0 -
 《时光书写N0.16》 布面综合材料/2021
《时光书写N0.16》 布面综合材料/202130 x 30 cm | ¥ 20,000
2.0 -
 《时光书写NO.4》 布面综合材料/2020
《时光书写NO.4》 布面综合材料/2020160 x 160 cm | ¥ 110,000
2.0 -
 《时光书写N0.18》 布面综合材料/2021
《时光书写N0.18》 布面综合材料/202130 x 30 cm | ¥ 20,000
1.9 -
 《时光书写N0.20 》 布面综合材料/2021
《时光书写N0.20 》 布面综合材料/202130 x 30 cm | ¥ 20,000
1.9 -
 《时光书写N0.21》 布面综合材料/2022
《时光书写N0.21》 布面综合材料/202230 x 30 cm | ¥ 20,000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