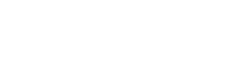杨小彦
董文通的母题不无残酷,又不无自然。他始终把目光盯住废墟,或者与废墟具有同一性的房子,和围绕着这些房子的景观。因为盯得紧张,盯得目不转睛,于是就演变成一场无言的逼视,一场洞察末日的凝视,一场有温度的平视,以及一场,在他心目中建业构起来的,诗意般不停地发生骚乱的对视。
其实,董文通不是对废墟有兴趣,那只是一个由头。他所执着的是往昔,是那些先他而在的,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的血缘痕迹,一代又一代地,既化身在基因中遗传至今,而且还要继续遗传下去,同时又固执地附着于曾经的生活之地、之房、之处、之物,让那些与生俱存的周遭环境无不打上母胎的印痕。他看到这些个印痕,然后,眼前的实物就在他的盯视中变成了永恒的镜像,而走向他年轻的内心,在大脑的视觉区搭建起一座又一座迷宫般的回廊。他就终日穿行在这些个回廊中,寻找着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伪的出口。
我蓦然想起了卡夫卡的“城堡”,不断地尝试着走向前去,不断地以为自己已经触摸到了粗糙的墙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落空,粗糙的墙壁在无限地向后退缩,以至于让寻找本身成为事实,徘徊其中而百感交集。
“家乡”就是董文通的“城堡”,不断地走近,以为达成目标后才发现,“家乡”还在远方、远方,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召唤着他,让他前行,让他思索,让他挣扎。于是乎,董文通用各种观看的方式走近他的“家乡”,所以才有了种种的盯视、逼视、平视和对视。他种种的观看状态一直停留在“家乡”的废墟表面,有力地形塑了具有样本意义的“记忆”的形状。这些个形状,就成为了董文通的作品,那些个油画、速写、装置和影像。
董文通一直在做的是,让“记忆”变成可以触摸的形状,然后,他就可以在遥望中把观看变成了眼前的“抚摸”。他从双眼中伸出一只无法窥见的手,然后,努力向前伸去,一直就那样,哪怕痉挛,哪怕窒息,也必须伸着,向前,再向前……
原来,记忆是有形状的。
拉康从镜像理论出发,试图论证记忆的起源,并把这一起源追溯到子宫之中。他认为人的成长有“二次认同”,第一次认同诞生在怀孕之际,带着子宫的暖流被抛向与个人俨然陌生的未知世界,开始了人生旅途最初的冒险。成长的第一个胎记既带有子宫的挤压,也包含着父母的抚摸,并最终形成初始的人格。接着,稍微长大了,必须走向社会,去托儿所,去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初始的人格受到了社会全面的捶打甚至欺压,原先的认同所形成的平台成为二次认同的开始,并在二次认同中完成人格的成长,以社会身份亲临种种隐含着叛变与眷念交杂的情境,体会着人生的严酷与兴奋。
其实,艺术家面对他的母题时,他已经完成了拉康意义的“二次认同”,他的艺术行为实质上是“第三次认同”,试图通过重新定义母题而获得一种永恒的力量,让本来飘忽的记忆实体化,成为摸得着的、有形状的存在。
在《还乡拾遗.系列创作之一》这幅油画里,一个应该是来寻找过往痕迹的成年人,正对着一堵嵌在墙壁里的柜子仔细辨认。画面近景的墙上挂着家庭镜框,镜框里大概放着家人在各处的合照,镜框上头则贴着几幅三点装女郎的彩色画片。熟知家庭布置的人们都知道,家庭镜框等于是家庭公开的历史,而三点装女郎的彩色画片则给出的房子的年代。盛行三点装挂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到了世纪末时,这一门曾经大红大紫的生意就突然式微了,基层民众的趣味发生了重大转移,于是三点装画片就成为历史的节点象征,贴在墙上,像时钟那样,把历史固置在某个动人的时刻。本来,在古旧的房子里贴着三点装女郎的彩色画片,本身就宣示着现代化的强行介入,引发了人们对物质主义的疯狂想象与追逐。然后,一切都过去了,飞速发展意味着丢弃,房子于是变成了废墟,只有墙上的旧物依稀可辨。有意思的是,董文通把探寻旧物的中年人又画了一幅,显示他对这一个人的姿势与有独特的偏爱,似乎他代表着一种努力。在《还乡拾遗.系列创作之二》中,探究者变成了一个摄影家,他正通过镜头把眼前的废墟给仔细地记录下来。在《还乡拾遗.系列之三》中,董文通又把探究者变成另一个中年男人,他在户外注视着曾经的住处,表情冷漠而又有点好奇。
关键是,所有这些入画的母题是通过照片确认的。也就是说,艺术家先是用镜头记录下眼前的旧物,然后再变成流畅的油画。照片的旧物是静止的,一旦转变成油画,就自有一种表现性在,从而突显了其中的荒诞。今天来看,艺术家通过影像从事表达已经不是问题。面对旧物与面对照片,在观看上可以具有某种同一性,让照片如旧物般发光。关键是观看者的立场,他能否意识到观看本身所蕴含着的意义。
从董文通的作品看,他对逼视、凝视、平视与对视并不陌生,他正是通过几个系列的作品,从摄影到平面再到装置与剧场效应,不断地把自己从这四种观看的方式中转移,以至于使观看本身因频繁变位而显出一种焦虑,一种缠绕着情感不断深入的焦虑。结果是,观看成为象征,作品只是这一系列象征的载体,用以陈述一段并非虚构的个人史。《遗落的世界之我的小学》系列,以及《被遗弃的学校》系列和《被毁坏的工厂》系列,其实是艺术家本人从小到大的那些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处所,也是他成长中无法模糊的节点,这些个处所与节点升腾到记忆中,竟然让记忆凝结成可以认真触摸的形状。董文通正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触摸,唤发起他内心的思绪,从而让记忆的形态外化为拍摄、描绘与摆布的对象以及观看的载体,让个人生存成为可以查阅的谱系,从而让世界在记忆中固置。
所以,从这一意义看,我觉得董文通拼其合力所创作的,其实只是一件作品,那就是“记忆的形状”,这个形态的细节散落在各处,董文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拍摄、描绘、装置,再拍摄、再描绘、再装置,让过往被遗弃的、被毁坏的岁月连同物质得以恢复,并屹立在世界之前,让尊严重新成为根基。
2017年11月23日深夜广州祈福
点赞 0 浏览 162
-
 《中国餐馆no.2 》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2 》 纸本彩墨/200739 x 52 cm | ¥ 45,500
3.3 -
 《中国餐馆no.11》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11》 纸本彩墨/200752 x 39 cm | ¥ 45,500
3.2 -
 《中国餐馆no.12》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12》 纸本彩墨/200752 x 39 cm | ¥ 45,500
3.2 -
 《中国餐馆no.13》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13》 纸本彩墨/200752 x 39 cm | ¥ 45,500
3.2 -
 《中国餐馆no.14》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14》 纸本彩墨/200752 x 39 cm | ¥ 45,500
3.1 -
 《中国餐馆no.15》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15》 纸本彩墨/200752 x 39 cm | ¥ 45,500
3.1 -
 《中国餐馆no.1 》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1 》 纸本彩墨/200739 x 52 cm | ¥ 45,500
3.1 -
 《中国餐馆no.6》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6》 纸本彩墨/200739 x 52 cm | ¥ 45,500
3.1 -
 《中国餐馆no.4》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4》 纸本彩墨/200739 x 52 cm | ¥ 45,500
2.9 -
 《中国餐馆no.3》 纸本彩墨/2007
《中国餐馆no.3》 纸本彩墨/200739 x 52 cm | ¥ 45,500
2.1